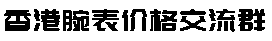昨天,也就是6月30日,是Beyond灵魂人物黄家驹在东京意外事故中去世的第24年。这些年来,Beyond受欢迎的程度并未减弱,相反,越来越多人开始喜欢Beyond,认同他们歌中的表达,那一种真诚的“乐与怒”(香港对摇滚的翻译)。
本刊曾在黄家驹去世20周年时派记者走访香港,探访他的生活和创作,以及他背后那个时代的香港的印痕。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13年第25期封面故事。
同时代的多数歌星都已经消失了,就连粤语歌也在全面式微,孩子们还唱着他唱过的歌。可是,黄家驹在天上,在忙什么?还在写歌吗?
![]()
黄家驹
在香港找寻黄家驹的足迹并不容易,尽管地铁里的纪念黄家驹的演唱会的“驹歌”海报巨大,海报上写着“我们都是听他的歌长大的”也让人心动,可是继续找下去,就会发现处处荒芜:黄家驹和他的兄弟黄家强长大的苏屋邨正在拆除;他读过的中学已经被一家崭新的酒店所取代;唯一重要的纪念场所,是黄家驹的墓地,正是6月,他出生和死亡的月份,堆满了歌迷送来的花束。
去遥远的将军澳华人永久墓地寻找黄家驹的墓地,光是爬山路就是一个多小时,远处是海,墓地是在规整的山头上,足足有几千座之多,看着心里发慌。疑心很难在这成千上万的死者痕迹中找到黄家驹的墓地,可后来发现担心多余,远远的山头之上,墓地的负责人用蓝白色的涂料在他那块小空间里刷了一遍,加上大堆的花束,并不难寻找。
一个黑衣服的女郎肃穆地站在墓地,她是一位宁夏歌迷,1986年出生,小时候只模糊地在电视里看到过黄家驹去世的消息,可是上初中的时候成了Beyond的歌迷,迷到了每次来香港只有一件事,就是来黄家驹的墓地祭拜,这次是6月10日,黄家驹的生日那天深夜到的。从宁夏出发来香港,即使在交通便利的今天,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她从银川出发去西安,要在机场等一夜,再飞往深圳。两天颠簸才能到达香港,拉着行李走到墓地的时候,正好有歌迷群在献花,黑夜里的花束只能依稀闻到芳香,对于迷恋者,这是每年不可少的仪式。
![]()
每年的6月份都会有各地的歌迷前往墓园祭奠黄家驹
她的正职是模特,所以自由时间比一般人多,走到墓碑后面,拿出香来,给每一位前来拜访的歌迷。墓碑是白色大理石的,顶端是一块雕刻的吉他,这是新墓碑,2009年,墓碑曾经被人恶意破坏过,白色的大理石遭到划损,当时黄家强受到指责,说他对兄长的墓碑被毁坏毫不关心。可事实上,黄家强很伤心,用各种原料来去除上面的污痕,可是无效。最后只能换上新墓碑,墓碑上的照片倒是老的,家强家中也放着同样的照片,戴着耳环的黄家驹,面带着微微有些孩子气的笑容,定格在他的年代里。黄家驹的朋友刘宏博告诉我,那样也好,他们不能想象家驹老了是什么样子,他就活在31岁里,什么时候、什么时代都永远是那个模样。
自从乐队诞生起,是与非就没有离开过他们,大概唯一的快乐时光,应该是尚不出名的练歌时代。那个练习唱歌的地方还在,歌迷们心目中经典的“二楼后座”,也是黄家驹去世后,乐队第一张专辑的名字。
我们去到“二楼后座”找寻黄家驹的影子,不过比较艰难。这里是一条卖花草的市场街,香港人叫“花墟”,优美的环境改变不了周围的人的烦躁,他们只是简单地告诉我们,晤知,晤知;更有横眉冷目的人说,不要来。
![]()
“二楼后座”外面的街道,香港人叫“花墟”
Beyond的成员叶世荣对我们说,上世纪80年代,乐队在这里练习的时候,“敌对情绪”就比较浓,因为乐队的排练实在太嘈杂了,吵了周围的邻居。这里是叶世荣的祖宅,是他祖母的物业,当时叶家出租了一部分,其中一小间给他们做排练房,也就是香港人所说的BAND房,叶世荣记忆中,当时的房间很小,因为其余的几个部分出租给房客了。
当时乐队还偏重金属和硬摇滚范畴,而且一练习起来就忘记了周围还有房客。有位房客老伯,他们管他叫“石山佬”,因为他爱玩假山石。老头一生气就来拍门,大声呵斥他们,叶世荣为了讨好老头,送了他一台旧冰箱,可是老头还是照旧来拍门,气坏了他们;还有警察接到投诉上门的,乐队安静了一小会儿,结果忍不住又拿起乐器排练,警察这次坐下不走了,聊了会儿天,发现也喜欢摇滚,结果开始听他们排练了。
慢慢地乐队有了乐迷,他们守在楼下。乐队买了外卖,外卖拿进来的时候,发现楼下已经有乐迷付了钱。这批乐迷,后来成为乐队最忠实的支持者,即使他们已经长大结婚成家,也没有放弃乐队,许多人的孩子现在也是乐队的乐迷。
乐队慢慢知名,不过还是没有钱,黄家驹和叶世荣他们几个自己动手装修房间,没有经验的他们直接用手和水泥,结果手差点废掉,因为水泥的腐蚀性很厉害;黄家驹去世后,这里被叶世荣改成了录音棚,名字就用“二楼后座”。
![]() Beyond最早排练的地方“二楼后座”
Beyond最早排练的地方“二楼后座”
坐着极古老的电梯轰隆隆上去,拉开铁拉门,门口挂着的乐队海报算是Beyond的标记,其余就没什么了,旁边是旧宅改造的廉价钟点房,倒还比这间有纪念意义的BAND房光鲜些,不过叶世荣并不在意,他说,这里留下来,就是薪火相传的意思,现在他,还有和他学乐器的学生们都会使用这里,这里是Beyond的平民精神的象征。
至于黄家驹和黄家强长大的苏屋邨则正在拆除中,我去的那天正逢香港暴雨,山上的泥水会聚成河流,更显得整个楼宇摇摇欲坠。不过,苏屋邨并非贫民窟,这里是政府公屋,60年代是香港普通市民的住宅,黄家驹的父母是一般市民,不富裕,可是也并没有多么穷困,是那个年代的一般家庭。
![]() 黄家驹儿时居所附近的街道
黄家驹儿时居所附近的街道
黄家强回忆,自己和家驹是家中最小的两个孩子,上面还有兄弟姐妹,都比他们大很多,他和家驹的童年娱乐,就是去后山上烤红薯、抓草蜢,包括在家里翻箱倒柜地寻找零钱,找到了就去游泳,当时游泳池的票钱是港币三毛,不知道为什么,常常就差那一毛钱,所以要在家里地毯式的搜索。
黄家驹姐姐的一段回忆,更能显示黄家驹的性格。他热爱的热带鱼跳到了楼下修车人的摊上,修车佬将之占为己有,并且逗前来索取的家驹说:跳到我家,就是我的;黄家驹一时生气,把修车佬的车胎从车上拿下,说:这也在地上,也被我捡到,算是我的吗?修车佬只能把鱼还给了他。黄家驹后来被称为“黄伯”,就是因为他会说道理,不少和黄家驹交往过的人觉得他为人处世圆融大方,并不是想象中摇滚乐手那么孤傲。
![]()
黄家驹(左)和黄家强兄弟在练琴
因为比黄家强大,所以黄家驹的兄长性格慢慢形成,他特别会照顾黄家强,以后发展到一切乐队成员。黄家强回忆说,家里的责难,比如玩乐队荒废学业啊,比如乐队噪音骚扰邻居啊,母亲都会去责难兄长,落不到他头上;黄家驹的会照顾人,体现到叶世荣身上特别具体,他是鼓手,本来不该他唱歌,可是当Beyond乐队刚红的时候,黄家驹希望每个人都能有更多发展,一定要叶世荣在他们拍的电影里面唱一首歌,自己帮他写这首歌曲。黄家驹就是那种大哥型的人,一定要罩着周围的人。
跟黄家驹交往的条件是,尊重他,他是个开朗而有幽默感的人,和谁都能说一大堆话,可是如果发现对方不够尊重他,他的态度会立刻冷下来,会开对方的恶意玩笑。叶世荣说,现在想起他当时的那些笑话,还是觉得很滑稽,不过,他的话大多有道理,并不是空说说而已,自然而然地,黄家驹聚拢了一批玩音乐的人,成了乐队的灵魂人物。
90年代在北京音乐台做“香港风景线”的奚志浩是在香港街头遇见尚未成名的Beyond的。他对我回忆,那时候他只是个爱音乐的16岁少年,喜欢逛唱片店,某日在汇丰银行对面的草坪上休息,看到四个长发青年向他走来,表情却很友善。“他们的气质,一看就是文艺青年,肯定不是那种卖保险的。”所以,他很愿意和他们对话。
![]()
Beyond乐队
几个人的名目是做音乐调查,问他爱听什么类型的音乐,买什么磁带,喜不喜欢摇滚,最后拿出自己的演唱会票子,只要10元一张,在一个不甚知名的礼堂明爱中心举办。奚志浩毫不迟疑地买了票,因为在见到Beyond之前,他和多数乐迷一样,几乎不知道本地有自己的摇滚乐队。
那是一场让他难以忘怀的演唱会。当时尚无大众知名度的Beyond却已经有了不少少女歌迷,因为她们特别喜欢尖叫,从头到尾没有停息。并且有自己的着装风格,常常被侧目,后来传媒索性给她们一个代号“妹妹仔”,代表某种不良文化,说到底,其实就是一群叛逆的青少年,对本港出现的反叛乐队有种本能的热爱。
不过少女歌迷并不是Beyond能成功的最主要因素。成功的,还是乐队和社会的某种共鸣,这种共鸣,从乐队开始成立起,就有了模糊的迹象。奚志浩分析,当时摇滚乐队开始大规模出现,是因为香港面临的问题太多,经济开始走下坡路;1997即将来临,大批人开始移民。周围的人谈来谈去就是如何脱离这个岛屿,所以摇滚乐队的音乐大多是冷硬的社会批判,歌曲中的情感很是凌厉。“可是黄家驹不一样,他和他的乐队带给人比较暖的感觉,就像他们早年成名的那首《永远等待》一样,他们也愤怒,也出离,但是他们对未来是抱有希望的。按照今天的话说,就是所谓的传递正能量。”
这种正能量,和黄家驹有很大关系。当时香港乐坛将唱摇滚的一律视为叛逆青年,觉得他们长发飘飘,都和主流社会脱离,不爱上学上班,只喜欢过自己的疯狂日子。可是Beyond乐队中,除了黄贯中承认自己小时候算是个叛逆少年,其他人从小到大都过着很正常的日子,基本上没有什么众人眼中的不良行为。梁翘柏说,最不良的,也就是不好好上班,去海边沙滩上裸泳,弹吉他,让周围的少女们尖叫着走开,实在也说不上什么。
![]()
高中时代的有型学生“王子”黄贯中
黄家驹的姐姐回忆,她告诉过家驹,音乐不是自己玩的,还要被更多人接受,只有大众接受了,才能进一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黄家驹和一般的摇滚青年不同,他愿意走进主流乐坛。黄贯中回忆,当时很多摇滚乐团,觉得除了摇滚别的音乐都一钱不值,可是黄家驹告诉他们,要让乐队能走下去,就得做一些流行上口的作品,音乐有不同的态度,除了愤怒,研究也可以啊。黄贯中说他听了茅塞顿开。
乐队在1984年之后开始逐渐走向主流,首先是乐队成员剪了长发,变得更乖巧了。黄家驹也不再是那个满面青春痘的年轻人,他变得热爱护肤,讲究形象。刘宏博说,有阵子家驹整天讲究护肤,在后台和交换做面膜的心得。后来Beyond的主要词作者刘卓辉也说,他和黄家驹去北京演出,同住一起的时候,第一次发现,男人也用这么多的护肤品。
![]()
Beyond成员一同荡秋千是难得的轻松时刻
不过,家驹并没有放弃自己对真正问题的思考。刘宏博说,他因为从内地出来,知道很多内地的事情,当时的香港青年,很少有对内地发生真正兴趣的,即使提出问题来,也都是表面的,可是家驹不同,他俩在一起,除了谈音乐,就是谈大问题。从永恒是什么,到中国究竟为什么落后,都在他们没日没夜的长谈中,家驹当时的女朋友嫉妒了,说刘宏博和黄家驹在一起的时间,比跟她要多很多。
80年代中期刘宏博回内地,当时内地还比较落后,坐飞机在空中看黄河、长江,并没有多少兴奋感,反倒觉得像伤痕,一回到香港,家驹就拖住他,让他谈对内地的感受。他把自己的感觉和家驹说了,家驹忙碌了几天,做出的音乐,就是后来让他们真正登上流行榜的那首《大地》。
黄家驹那时候在想什么?刘宏博说,他似乎和外界关系很疏远。香港乐坛流行什么、电台每日讲什么,都和他没有什么关系。他自己作词作曲,有种浓厚的苍凉感,也很慈悲为怀。他的脑筋,不在香港,一会儿在北极,一会儿在中原大地,他爱读唐诗宋词,完全与香港流行文化迥异。要不是来自北京的背景,他觉得自己也很难与家驹做朋友。
黄家驹显然有以世界为家的情怀,香港束缚不了他,出名也没有改变这点。1991年,家驹和慈善团体去了非洲,写了两首著名的歌曲:《光辉岁月》,;还有《Amani》,斯瓦西里语“和平”的意思,呼吁世界和平。同为作词者的刘卓辉后来写道,看了这两首歌词,他觉得黄家驹就是天才。朱耀伟说,他发现黄家驹的歌词,在后期越来越好,是因为他找到了自己的一种表达方法,不再为外界的戒律所约束。
![]()
1991年9月在香港红馆举办“生命接触演唱会”时的黄家驹
香港乐坛慢慢接受了这位“乐与怒”(香港对摇滚的翻译)的代表乐队,情歌虽然还是乐坛的主流,但是随着社会的变化,对社会不满,开始呼唤亲情、友谊,乃至社会平等、世界和平的歌曲开始有了容身之地。有人分析过,乐队在香港100首流行金曲中上榜的6首曲目,全部与爱情无关,带有浓厚的社会批判色彩,并且坚守公义、道德和理想,所以一直流行到了今天,这和黄家驹的个人思考有很深的关系。
除了歌词,黄家驹还有许多吸引人的特点。1988年,作为香港摇滚音乐的代表Beyond来到北京开演唱会,当时音乐台的主持人朱云去采访,发现这乐队怎么这么不摇滚啊,看上去很乖,穿着也普通,不过很快,她看见了黄家驹的特殊性:“他很聪明,很稳重,乐队由他来回答问题,虽然不叛逆,但是注定是会红的那种摇滚乐队。黄家驹身上,有点摇滚,有点华丽,有点批判,有点理想,单项可能比不上别的乐队,但是组合起来就高人一头了。说到嗓音,他也会扬长避短,不够高,就用特殊唱法,你比如说那句出名的持续的‘欧’,就很聪明。”
他真的穿着很普通,以至于演唱会开始的时候,武警不知道他就是主唱,不放他进后台。后来他们的形象才慢慢改变,刘宏博出了不少主意,让他们戴些首饰,很东方的标志,不日本化,慢慢地成了日后我们熟悉的形象。
![]()
从早期的简单造型到后期的时髦造型,黄家驹的形象变化很大,但不变的是音乐精神
那次演唱会,刘卓辉一直跟着。当时的北京还不太开放,黄家驹他们的行动,时常受到主办方的制约。有次调音还没有好,主办者就催促乐队上场,并且非常严肃地说,如果推迟5分钟上场,骚动出了问题黄家驹要负责。可是他坚决不上场,一直到音响全部调好。他是个要求完美的人,容不得自己出错。那次,他还用普通话演唱了《一无所有》,也见到了崔健。
不过,崔健对他的印象不深刻,那是黄家驹尚未完全长成的年代,1988到1993年,他生命的最后5年,是他的音乐才能全面爆发期,整个乐队以他为主一共写了500多首歌,现在拿出来唱的有100多首,还有大量没有发表。这些发表的里面,多数经典流行到了现在。
不过他成为主唱的最关键原因,是他嗓音里的热情。刘宏博说,家驹几次失声,消了炎之后,每次都比以前更沧桑,也更雄厚,他会给自己的嗓子注入特殊的力量,因此特别有感染力。黄家强的嗓音和他很像,可是,黄家驹去世后,乐迷还是觉得,他的那种特殊是无人可以模仿的,即使弟弟也不行。
![]()
黄家驹
多年之后,他自己去青海游玩,在一个破烂的长途车里,听到司机大放黄家驹的歌曲,这时窗外阳光灿烂,他说家驹在的时候,其实他没有认真听过乐队的歌曲,因为就是听听大样,正式发行反倒不太会认真听了,可是这次,他听得非常认真,一边听,一边流眼泪。
他的疑问,和我们在墓旁遇见的歌迷一样,家驹在天上,在忙什么?还在写歌吗?
⊙文章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欢迎转发到朋友圈,转载请联系后台。
点击以下封面图
一键下单「我们如何踏准财富节点」
![]()
▼ 点击阅读原文,今日生活市集,发现更多好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