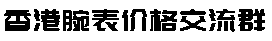五 打不着火的枪
我现在回忆过去,只能追溯到上高中的时候,再往前,事情是清晰的,时间是模糊的。我需要做一张表格,把高中、初中、小学的就读时间排下来,再把记忆中的点滴填上去,才能得到大致的时间。
这样推算的话,当我哥带着我来到村外的田野,试验他造的第一把枪的时候,大约是在1993年的春天。那是一把非常简陋的手枪,铁丝弯出枪身和把手,像一幅简笔画,上面裹着厚厚的橡皮胶带。枪管是用自行车链条拆散后拼起来的,里面塞着一根白炽灯灯芯做的子弹,灯芯内部填满了从火柴头上刮下来的火药,子弹后面裸露着枪栓,贴一张从火柴盒上撕下来的摩擦条,然后是一根在橡皮筋上蓄势待发的火柴,再后面是我哥那张胡须初生的坚毅的脸。
“你站远点,一、二、三……”
嘭!!——我哥的手上腾起一阵白烟,他的手掌被炸了个对穿,他蹲在地上咬着牙,额头的筋都绷紧了,冷汗直流。
科研工作暂停,我哥缠着绷带和我在家愉快地玩耍。他叫我找来一个健力宝易拉罐,剪开当锅,倒上白糖和猪油,在炉灶里烧,融化成一摊吉红色的饴糖给我吃。他又找出几把匕首,教我练习飞刀术,隔着十步一甩,让匕首稳稳地扎在木板上。这段时间妈妈都没有拦着他,甚至对新发现的匕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一个月后,妈妈一层一层揭开哥哥的绷带,我在旁边盯着看,那手掌变得又白又嫩,中间只有一点凹陷。
于是哥哥又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火枪的研发工作中。
他不断完善细节,用自来水管做枪管,找来了模具,把铝饭盒熔化,铸造出非常正式的枪把和枪身,但是对于火枪的核心技术,也就是怎么让枪打起来这一点,他始终未能参透。子弹需要底火,底火需要高科技,一个一穷二白的小古惑仔是没有这个能耐的。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他会跟着村里的大人一起去市区看枪毙。他会蹬着自行车跟在游街的囚车后面,耐心地穿过大半个城区,忍受着高音喇叭里的罪行通报和严打口号,直到到达法场,直到高大的武警把囚车上那些比我哥大不了几岁的年轻人拖下来(他们头上插着木牌双手缚在背后),砰得一声就地枪决。然后人群散去,我哥就在血迹旁边寻找弹壳或弹头捡回家。但那些都是已经用过了的,薄薄的黄铜里只有炸药的残灰,他百思不得其解,只好叹着气把弹壳扔在抽屉里。还有他的枪,永远处在半成品的状态,上不了帮派的战场,成了我的玩具。
六 孤独的冲压机
回想过去,我觉得哥哥那时肯定是苦闷的,他执着地造刀造枪,不是因为喜欢这些,而是想要寻找一条出路。
,改革春风吹遍大江南北,在温州似乎做什么都能赚。我们村里的房子家家户户门前都有道坦,也就是小院子,平常都是我们小孩子玩耍的场所。没多久,家家户户都搭起竹棚,把一座座小院子围起来当工厂,顶上铺着黑色的油毡布,旁边放着柴油发电机、油桶和机器。有做皮带扣的,有做打火机的,有做袜子的,做鞋子的最多。笨重的柴油发电机声音巨大,震动激烈,大人们在上面铺上石棉瓦,我们又有了新的乐趣,把小石头放在石棉瓦片上,只要机器一响,这些石块就像活过来一样,疯狂地跳舞。
人们也在疯狂地赚钱。三叔家门前,每天有好几辆三轮卡开过,运来成梱的锋利的铜皮。司机和小叔一起把铜皮抬下来,那是别的工厂的下脚料,正适合制作铆钉。铜皮分给在作坊里打工的七八个江西姑娘(她们是头一批到我们村来的打工者),沉重的冲压机冲头每秒钟跳动三四次,每次都会发出沉闷的轰鸣,她们嘴上戴着口罩,耳朵塞着棉花,手上戴着袖套,就着昏黄的白炽灯,准确的在三分之一秒的间隙把铜皮推到冲头下面,裁出一枚枚比指甲盖还小的铆钉、铆座。从早上六七点到晚上八九点,中间吃午饭晚饭。晚上九点以后,一台台冲压机陆续停下来,嘈杂的交响也变得清晰,你可以按照节奏听清有几台机器在运行,三台、两台、一台,最后这台会倔强地持续十几分钟,或者半个小时,那是当天没有完成定量工作的、或者想要多冲几斤铆钉的姑娘还在坚守,慢慢地,你能听得清马达转动的嗡嗡声,冲头吞掉铜皮的类似折纸的响声,以及机器重新抬起,在滑轨上移动的声音——叽工、叽工、叽——工……
妈妈也在三叔的作坊里打过一两年工。那时她原来工作的在直洛的汽配厂已经倒闭了,后来又在仙桥的鞋厂里踩鞋帮,再后来就在三叔的作坊里冲铆钉。相比之下,我当然是喜欢她踩鞋帮的,因为车间里很明亮,到处是做鞋帮的海绵,我可以随地打滚,缝纫机嗡嗡响像一群蜜蜂,不会伤人的耳朵,最重要的是,车间里有台磁带录音机还会不停循环播放流行歌曲,为单调的工作增添节奏感。
那时候北京亚运会刚开完不久,韦唯和刘欢演唱的《亚洲雄风》几乎在厂里播放了整整一年,我妈和她的工友们就在雄壮的歌声里把冒牌的亚运会LOGO一个个缝在鞋帮上,雪白的棉絮四处飞扬。
冲铆钉就无聊多了,冲压机都是并排靠墙放着,妈妈工作的时候我只能看到她的背面,在油渍斑斑的工作服下,她的肩膀不停抖动,机械地移动双手,抓过一张铜皮,钉成马蜂窝,摞在左脚边,再伸手去右侧拿新的铜皮。因为就在家旁边,所以也无所谓什么时候下班,妈妈总是整个作坊里最后一个回去的。晚上我不敢一个人睡觉,就在妈妈旁边百无聊赖地坐着,一会儿扯扯她的衣服,问她什么时候下班。她在那摞废铜皮上比划一个高度,说,堆到这么高就可以了。于是我就有了目标,过一会就拿手比一下。在等待的时候,我困意重重,盯着冲压机的灯光在墙壁上投下来的,我妈妈巨大的影子,抵抗睡意。
七 非宗的名牌鞋
三叔的作坊在我们家族里只是一般般。我小叔比他起步晚,但发展快得多。他进了大批鞋帮、鞋底和香蕉水等原料,粘成一双双旅游鞋。堂屋里、厨房边、院子里到处摆放了用来晾晒旅游鞋的竹架子,一只崭新的竹架,不消三天就挂满了从鞋子上流下来的尚未冻结的鞋胶,空气中充满了苯类挥发性胶质的气味,刺激着人们的鼻子,让人既兴奋又疼痛。第一年,小叔搭着大伯的顺风车,把鞋子卖到了东北,收款的时候他怕出事儿,和我三叔一起坐火车过去。回来的时候,两个人用扁担挑着一个巨大的麻袋。麻袋沉甸甸的,他们从东北扛到了家里,在家门口,小叔自豪地把麻袋打开,里面全是银光闪闪一块钱硬币,足足有一万元。
聪明的小叔是特意把钱换成硬币的,那时候东北不太平,这样就算路上遇到了劫匪,也抢不走这么沉的一袋钱。
小叔和大伯相比,又差远了,,有全村唯一一台手摇式电话。他还驾驶着村里唯一的一台拖拉机,经常以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开着拖拉机到上海办货,是村里见多识广的人,也是第一个建起三层高楼的人。
三叔、小叔办的是作坊,大伯办的那可是正儿八经的工厂,白底黑字的厂名牌匾就挂在家门口,叫温州某某某鞋厂。大伯的生意多到忙不过来,村里老老少少都过来帮忙。我和堂姐堂妹们放学、放假了以后也常去大伯家里打零工。院子里总是堆着成箱的鞋子,准备发往外地,前厅里,男人们总在不停地给箱子打包,银光闪闪的打包机,像一辆小火车沿着扁平的塑料打包绳行驶,前后绕一圈,就包地严严实实。
女人和老人们在里屋做商标,楼梯下原来放马桶的小间成了仓库,里面放着打包成袋的各种商标,有正在跳跃的豹子,我们叫“猫”;有系着领结的兔子,叫“兔头”;有三个斜方块拼成一个三角形,叫“方块”;有三瓣的莲花,就叫“花”,还有大胡子老头叼烟斗(老人头),头发乱糟糟的美女(美人头),小汽车、小鲸鱼一大堆商标。一双鞋子很多地方要用商标的,侧面要用缝纫机把商标缝上去,上面,也就是鞋舌的位置,则是用油印机印上去的。这个活儿最轻松,基本上都是由我们小孩子来做,一刷,彪马;一刷,花花公子;一刷,鳄鱼……让人特别有成就感。我们赚到了钱(最多五毛),就去买糖,然后拿着捡来各种商标玩,从小学到了勤劳致富的道理。
虽然在同一片屋檐下长大,但家庭的条件不同,孩子们的感受还是很深刻的。我大伯的儿子,也就是我堂哥阿文,比我哥大一岁,当我哥还拿着砍刀在隔壁村闯江湖的时候,他已经跟着他爸到各地做生意了。有一年冬天,快过年了,堂哥和大伯也从东北收款回来,和小叔不同,他们坐的是飞机。我们第一次见到做过飞机的人,都赶紧跑到大伯家里看。堂哥看起来太胖了,身体好像气球一样鼓。大妈帮他把羽绒服解开,我们才看到堂哥前前后后裹着成梱的钞票,就像一件防弹衣。堂哥如释重负,打开行李箱拿出飞机上发来的草莓酱给我吃。草莓酱太少,我们都想要,他就问,你们今年谁最乖啊?我们都喊着,说自己印了多少兔头、多少花。我也很急,看到堂哥的鞋子,赶紧说,我印了很多方块,和你的鞋子上一模一样。堂哥说:不一样,我这个鞋子是正宗的。我问,那我们的鞋子呢?堂哥说,那是非宗的。
八 我们共同的爸爸
我们给大伯家印刷商标的事,哥哥是从来不参与的,尽管他穷得叮当响,但从不屑于赚这种小孩钱。这也成了家里和四邻攻击他的借口。
真正有出息的人,要么勤快,比如像大伯和小叔们那样,能做出很多非宗鞋,赚很多钱;要么路要走得正,比如像我们亲戚们那样,凑钱入股走私电子表,只要走私两三次,就能买辆本田王摩托车了。再不济,就是像我妈我爸一样出力气,也能攒下不少钱。但我哥是不屑的,不仅仅因为来钱太慢,更因为他和堂哥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当年一起捣蛋时候,堂哥是他的跟班,现在又怎么可能给堂哥家里打工呢?
很多年以后,我妈和我聊天,她说,有一次我哥和我堂哥不知道又捣了什么蛋,惹得我大伯非常生气,把他们两个都扔到河里去了。堂哥一掉水里马上往回游,被我大伯捞起来又扔了回去,我哥观察了一下,看到这种情况,直接就游到对岸去了,爬上岸上又蹦又跳,。堂哥再次游到大伯脚下,向他求饶,说我错我再也不敢了,大伯就把他捞上岸来。
大伯揪着堂哥回了家,见到了我妈,这时候我哥也满身湿漉漉的站在旁边。大伯说了一句话,让我妈耿耿于怀很多年,他说:这两个小子都挺聪明,我儿子聪明在骨里,你儿子聪明在皮里。
大伯说完就走了,我哥向我妈抱怨,说大伯偏心,把堂哥扔得近,把他扔得远。我妈愤怒地说,他又不是你爸,凭什么不偏心?
这句话戳中了要害。我从小就知道,或者被我妈灌输,那个我和我哥的共同的父亲,我妈妈的丈夫,是指望不上的。我爸一岁的时候生过脑膜炎,反应比别人慢一拍,从小也没有上过学,酗酒,脾气暴躁,干的是采石场里面的体力活,他唯一擅长的就是卖力气。我记得有一次村里的公厕满了,全村组织挑粪大赛,就是把粪肥运到田里去。我爸挑着两桶大粪健步如飞,像一台散发着恶臭的火车头,跑在全队的最前面,并光荣得戴上了一枚大红花。我从没有见过我爸这么快乐,但我妈对此绝对嗤之以鼻,因为她觉得这是村里组织的,没有奖品,干得最好,恰恰说明他最笨。
我妈是如此地痛恨我爸,我们甚至都从没叫过他爸爸,而是和堂弟堂妹们一样,叫他“二大”,也就是“二叔”意思。小时候,当我发烧不肯打针,拉着裤子挣扎的时候,我妈就会吓唬我,不打针你就会变得和你二大一样,我马上就脱了裤子。他们结婚39年之后,我妈59岁,她为自己在汀田的娘家后山公墓上选了一块墓地,这样死后就不用和我爸埋在一起了。
但是我们的内心,总还是有那样的需要。在我整个童年的记忆中,保留着两次拥有爸爸的感觉。一次是秋天和家里人收割完稻谷,我捡起几条遗落的稻穗,用火烧着玩。饱满的谷粒像爆米花一样炸裂,露出诱人的白肉。我爸看到了,坐在我旁边,说他们小时候也这样玩,烤过的谷粒很好吃。还有一次,午后我在村里的小路上奔跑,正好撞到爸爸提前下班回家,他似乎很高兴,把粗糙的手掌在我面前摊开,里面是一只他在路上捡到的塑料小金鱼。我非常开心,爸爸也很开心,一把把我抱起来往家走。不知道为什么,那一时刻,我对他没有恐惧,心里还充满了自豪。
我不知道我哥是否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那些短暂的“拥有爸爸”的时刻。我只知道,在整个童年,我都是如此渴望拥抱,他应该也是一样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