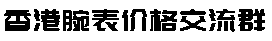第八章 佐的黑暗世界
祖父说,不要妄图找出真相,真相往往会令你心痛。但是我,一次又一次的突破安全界限,去逼近扭曲的事实,这或许就是我的不幸。
我叫佐,单一个字。或许我还有别的名字,但是从祖父口里我只听到佐这个称呼。祖父是我的人生法则的制定者,他把佐这个名字赋予给我,就像他给世间万物重新命名一样,我只是其中一个。
8岁的时候我就来到这里,至于8岁之前,记忆里是一片空白。在记忆中我一睁眼就在一个破旧的小木屋里,我躺在一张木板床上,微弱的烛光在黑暗里摇曳着,映射在天花板上的我的影子蜷曲着像一只诡异的猫。床靠着窗户,我拉开帘子去看,把耳朵贴在玻璃上试图听到一些人声,窗外是一大片的黑暗,有鸟兽在森林里追逐不断摩擦着树叶发出沙沙声,还有一只叫的特别厉害的鸟不停地在扇动翅膀的声音。天空上挂满了星星,在这里,似乎是靠星星银色的光来照耀森林的。
一只硕大的鸟从天空划过,拍打着翅膀直冲而下,就在刹那它略过窗户,凶狠得盯了我一眼。我惊得向后退去,这不是一个人呆的地方。我开始对自己的处境害怕,这时候进来屋子的门开了,我的祖父进来了,他把窗帘拉上,坐在床,头给我盖好薄被子。这是我第一次见他,但是我的意识里就出现了祖父这两个字。
后来我发现这里不全是每天都有星星的,没有星光的时候,外面一大片丛林都被黑暗笼罩着,丛林里住了形形色色的鸟兽。我不知道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地方,整天整天的看不到太阳,我那时候甚至不知道太阳,只是在书卷上看到过一副后裔射日的图画,其实是一颗都不剩了吗?
祖父说,一颗都不剩。他那会儿已经60岁了,显得非常苍老,两鬓都是白发,脸上叠着一层层的皱纹,就像是一个皱纹人。但是他的眼睛却是十分敏锐的,在黑夜里炯炯有神得发出光芒。他常常拄着拐杖去森林里面喂养那些鸟兽,每当他的拐杖击打着地面的时候,他就将我锁在屋里。用一把沉重的铜锁紧紧扣上,我尝试过用屋里所有的工具,事实上,像是嘲讽般,锁是在门内的,他走出去的时候,锁就自然地合上了。并且屋里摆放了许多工具,角落里甚至有一把大榔头,我用那把大榔头也不管用。我意识到这是一把我永远都打不开的锁,这把锁只听从于祖父,而我就是被锁关住的提线木偶,我的人生只能听从祖父操作。
在我11岁极其寻常的一天,祖父出门了,但是他并没有带上拐杖,他穿着一件大衣,厚实的帽子裹住他光秃秃的脑壳,很奇怪的是锁并没有在他走之后合上。他只是叮嘱我要小心些,最近最有飓风。对外面世界充满好奇的我,早就按耐不住了,那把铜锁歪开一半,我轻轻地将锁取出来,收进口袋里。走之前我环顾了一下屋子的四周,带走了一个指南针,一个电子表,一些面包,还有在角落里放的祖父的拐杖。一出门便有巨大的风迎面而来,看来是刮飓风,这里的天气总是让人琢磨不透,我将脖子上的围巾打了一个难看但是牢固的海带结。
我的计划是一直向东走,逃离这片森林。电子表显示现在是凌晨,我将指南针对准北极星,定位东边的方向,指南针细小的针尖直指向那片森林。无疑,我得穿过这片森林才能到达东方。我庆幸这会是深夜,有一大片星星笼罩着上空,抬头望的时候,这种漫天繁星的景观确实是吓人的壮观,多望几眼便容易沉迷进去,有那么会我的内心动摇了一下,但是低头望向那片无际的黑暗森林的时候,内心便怀揣着恐惧了,这不是一个天堂,而是地狱。脚下的路在星光下倒是能够辨析,只是在深夜森林中藏着几万只正在打盹的野兽,只要我一不留神,便会被一口吞进,不留残渣。
其实我在小屋里最希望找到的便是手电筒,但是很奇怪,祖父出门似乎从不需要任何照明的物件,就连蜡烛都好像是为了我特意准备的。现在,没有任何照明的我,只能凭借嗅觉,触觉还有勉强能照得出路的星光,在森林里穿行。准确的说,森林里并没有一条准确的路,没有那种人为踩出来的路径,每走一步都是新的。飓风吹的落叶沙沙作响,有一些树已经被吹的一叶不剩。尽管我每走一步都尽量的抬起腿轻盈地放下,但是还是免不了听到踩在落叶上咔嚓的声音。这声音虽然微弱,但在我耳边却像雷鸣般醒目,使得我的行走速度缓慢许多。
我看了下手表,实际上我已经走了将近一个小时,但是并没能走出多远。我的眼力似乎变得愈发敏锐,走到这里还能隐约看到小木屋屋里的烛光,那是我故意留的,以便给自己一条退路,蜡烛大概只能撑得住三个小时,也就是说三个小时后,我便彻底没有回头路了。也好,我心里暗想,离开这里的念头越发强烈。
手腕上的电子表不停地向前推进着每一秒,在两个小时之后我的脚步已经比先前从容了许多。再回头望的时候,连那微弱隐约可见的烛光都没了。看来要走到森林的中心了,我深吸了口气,这里潜伏着最多的猛兽。小木屋里有一个书架,上面有上下卷的《森林物种溯源》,里面便记载了森林里上万种的野兽,在来之前,我才阅读完上卷,里面描述的野兽的外貌和行径便已经让我畏惧。
飓风让我步履艰难,我不得不抱着一棵接一棵树向前走,飓风吹起的那些沙子总是吹到我的眼睑里,膈得我难以睁开眼。又一次飓风吹了过来,我紧紧抱住眼前触手能及的这颗巨大的树,这棵树却开始膨胀起来,渐渐的,我的手圈不住被弹开来。树继续膨胀起来,挡住了我的去路,我在原地不敢动弹。随着一声啪嗒的巨响,树从里头开始向外裂开,树皮四溅,我匆忙躲到另一棵树的背后。没想到一经我的触摸,手里的这棵树也开始膨胀,并且迅速绽裂开。
我记起《森林物种溯源》上卷里面描述过一种叫“齿”的兽,它一生下来便钻到那些巨大的柏树中去,以树肉为食,在树的体内慢慢长大,一棵树被吃的差不多它们也基本就成年了,等到它们母亲轻轻摩树的表层,它们便如同听到呼唤,纷纷破树而出。看来我是不小心召唤出“齿”了,我的内心暗自懊悔。
这两只“齿”迅速包围住我,它们的个头还只是我的两倍,看来还只是两只幼“齿”,浑身是枯树的模样,灰褐色的条纹爬满枯树模样的表皮,裂开的嘴巴里露出两排整齐的锯齿。大概还处于磨牙期,两只幼齿的锯齿摩擦着,如同两把锋利的锯子发出卡咋卡咋的声音。11岁的我估计还不够两人撕咬,磨牙的。
我恐惧得连连向后退,帆布鞋子踩在成堆的落叶上,一个不小心便打滑了,一屁股坐在堆积如山的落叶里,我的身躯被落叶给掩埋了。我从落叶堆的缝隙里看到那两只齿正东张西望,疯狂地用锯齿咬开一个个柏树。从那些柏树里又出来几只齿,齿的队伍越来越大。躲在落叶里已经不再安全了,我的手赶紧撑着地面想要站起来,怎知道,落叶堆开始慢慢向上突起,在我的屁股下有一个物体的力量在顶着我向上。一个力量将落叶抖开,我才发现我正坐在一只猿猴的脑袋上。
这是一只小猿猴,在星星的微光里我能看到它的蓝色瞳孔,在《森林物种溯源》里我看到对于这种蓝色瞳孔的猿猴的描述,这是猿猴的一种变种,因为长期生活在黑暗中,瞳孔就演化成了蓝色,以便在黑暗中得到更敏锐的视力。这时在我们的周围已经包围了近十只齿,它们的牙齿一个个磨得锋利,正等着磨牙的食物。我屁股下的这只猿猴也慌了,一个动作向上跳跃到树上,我已从脑袋滑落到了猿猴的后背处,两只手死死锁着它的脖子,两只脚勾在它的腰部,活脱脱是一只小猴子。
蓝眼猿猴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巨大的晃动惊得树上的鸟兽都纷纷苏醒过来。一时之间森林在午夜苏醒过来,一声狼叫划破天空,我似乎成了众矢之的。我唯一可以依托的便是身下的这只猿猴,它大概也感觉到了我的累赘,在跳跃的过程中不停地剧烈晃动身子,抖动背部,想要把我甩出去。我的手已经渐渐没了力气,但是依然拼命抱住它的脖子。在剧烈的甩动中,我的眼泪都从眼眶中挤了出来,咸咸的划过我的脸庞,被飓风吹过咧咧地生疼。
蓝眼猿猴一会从树上转移到了地下,两只手抵着地面向前跑动,我的脸部贴在它的背上,早已变得扭曲,左手手背处被树枝划伤,鲜血从伤口处渗出来。我贴近它的耳畔,嘴里念着“救我”,下一秒我就嘲笑起自己的愚蠢,它如何能听懂我的话,我只能趴在它背上,听天由命。像是突然间受到了恩赐,这之后它没有刻意甩动背部了,相反更加集中精力作战,一边跑着一边朝后面丢枯枝,果然几只幼齿放弃追逐开始啃起枯枝叉来。但是我的鲜活的血液引来了狼的狂乐,几只唾液垂涎的狼从远处的山丘上飞驰而来。血腥味随着猿猴的跑动,从我的手背蔓延到森林各处。一场森林的食物狂欢正蠢蠢欲动。
星星在头顶上愈发闪耀,森林的道路上,树与树之间的缝隙组合成不同的小路,每条小路上都堆满了厚实的落叶,银色的光挤进这些缝隙中,铺在去向不一的小路上,森林间就像流淌着一条银河,我们就在这条银河上随波逐流。
越过一个横置的法桐树干之后,蓝眼猿猴的步子渐渐慢了下来,它大口喘着粗气,端坐在地面上,我依然死死挂在它的背后,紧张使得我的双腿变得疲软。我朝后看,在法桐树干的那头,以几匹狼为首的森林猎队在原地站立着,银色的星光下,那几匹狼镀银的唾液从嘴角边垂涎下来,但是它们没有再朝前迈进一步。
一阵狂躁的鸟的嘶吼从背后传来,法桐树干那头的猎队调转了队伍的朝向,朝另一个方向疾驰而去。
转载需获作者授权
欢迎大家分享到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