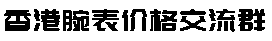飞毡
作者: 西西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6-1
定价: 58.00元
本书是西西长篇小说代表作,2005年获《星洲日报》世界华文文学奖。全书以花氏家族兴衰作线性的串联,配以魔幻现实主义和童话写实的手法,书写香港(肥土镇)百年世俗生活史。
香港标志性作家西西——王安忆称她为“香港的说梦人”,梁文道说,如果有人问香港有没有文学,有没有了不起的小说家,他会推荐西西,艾晓明认为在世的华语作家中西西“有资格获诺贝尔文学奖”。如果你想知道一个女性作家的视野有多广阔、笔法有多细腻,如果你想知道华语文学结合西方特别是拉美文学写作技巧可以达到什么样的高度,你一定要读西西。
香港20世纪的“百年孤独”——在《飞毡》中,香港化名“肥土镇”,仿佛马尔克斯的马孔多,“肥土镇”这个地名出现在西西的不同作品中,是西西创造的**代表性的意象之一,本书则是对这一意象*为全面而宏大的书写。肥土镇即是香港,巨龙国则对应中国大陆,通过《飞毡》,我们不仅可以窥见西西文学创作的核心,亦可以了解香港市民社会百年来的兴衰万象。
书名《飞毡》,严格说来,应是《飞毯》。毡与毯,音和义皆有别。
先说毡。何谓毡?我国古代制毡,是把羊毛或鸟兽毛洗净,用开水浇烫,搓揉,使其粘合,然后铺在硬苇帘、竹帘、草帘或木板上,赶压而成。《说文》之解释为“捻毛也,或曰捻熟也。蹂也,蹂毛成片,故谓之毡”。《释名》说“毛相着旃旃然也”,称为毡。《考工部》说:“毡之为物,无经无纬,文非织非纴。”
毡并没有经过纺捻和编织加工的过程,纺织学上称为无纺织物。它的出现,远比任何一种毛织毯为早,新疆地区气候较冷,在原始社会时期,已经广泛使用。公元前一千年的周王朝,宫廷中已设置了“共有其毳皮为毡”,监制毡子的官吏,称为“掌皮”。
毡是无经无纬压成之物,如今居室所用的blanket,即毛毡。一般手工用的felt,也是毡之一种。毡音沾,异体字为氈[编注:原文为“氈音沾,异体字为毡”]。
次说毯。毯也是用羊毛或鸟兽毛制成,却经编织过程。织法大致分两类:一为经纬平纹组织法,一组经线与一组纬线平行交织;相当于如今几桌上用的衬垫物mat,或置于门口地上用之蹭鞋rug。二为栽绒法,主要是在一组经线二组纬线织成的平纹基础组织上,再用绒纬在经纬上拴结小型羊毛扣,即如今一般所称之地毯,carpet。毯音坦。
毡或毯,在我国古代,有许多不同的名称。先秦时,称之为纰、罽、织皮。《逸周书·王会解》中提到伊尹向商汤建议,跟四方各地交换或贡献物品时,要“以丹青、白旄、纰罽、龙角、神龟为献”。“纰罽”即毛织品,罽,还是华采毛织品的总称。《说文》中解释为“西胡毳布也”。《尚书·禹贡》记载有“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织皮,不是地名,而是毛布,制造者是织皮人。
汉唐时,氍毹与毡常相提并论。张衡《四愁诗》中说“美人赠我毡氍毹”;汉《乐府·陇西行》诗曰“请客北堂上,坐客毡氍毹”。而毡毯这种毛织品的铺设位置、用途也不明确。《乐府》句中的“坐客毡氍毹”,是指铺在地上的织物,而“毾五香木”则是铺于坐卧家具之上的垫褥。唐代诗人岑参在《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鋋歌》中写道:“高堂满地红氍毹,试舞一曲天下无。”显然是铺在地上的毯;而《玉门关盖将军歌》中写道:“织成壁衣花氍毹,灯前侍婢泻玉壶。”分明是壁挂了。岑参乃边塞诗人,身处边疆,当然多见氍毹。而身处中原的杜甫,笔下是常见的毡。《与任城许主簿游南池》中写道:“菱熟经时雨,蒲荒八月天。晨朝降白露,遥忆旧青毡。”这是杜甫游齐赵时所作,秋天来了,遥遥怀念故乡,有什么比老家的青毡更温暖呢?青毡,乃穷等人家的御寒物。
明文震亨《长物志·绒单》曰:“绒单,出陕西、甘肃,红者色如珊瑚,然非幽斋所宜,本色者最雅,冬月可以代席。狐腋、貂褥不易得,此亦可当温柔乡矣。”富贵之家,当然以狐腋貂褥保暖,一般人则以绒单代席。绒单,由毛织成者曰“毛绒”,由丝织成者曰“丝绒”,绒单即绒毯,也即是毡。清李斗《工段营造录》曰:“铺地用棕毡,以胡椒眼为工,四围用押定布竹片,上覆五色花毡。毡以黄色长毛氆氇为上,紫绒次之,蓝白毛绒为下,镶嵌有缎边绫边布边之分。”可见毡也分等级,青毡当属蓝白毛绒,为下等毡,边镶也必定为布边。杜甫《戏简郑广文兼呈苏司业》诗中写到这位“诸公衮衮登台省”的广文先生:“广文到官舍,系马堂阶下。醉则骑马归,颇遭官长骂。才名四十年,坐客寒无毡。”青毡已为日用必需品,可是广文先生官独冷、饭不足,连青毡也无以奉客。宋王禹偁另有诗句云:“除却清贫入诗咏,山城坐客冷无毡。”七言中融嵌五言杜句,但易一字。无毡之苦,诚然古今共通。
区区一毡,已反映炎凉世态。然则读者看我抄书抄到这里,只怕已如坐针毡了。这种苦,当比冻寒无毡更难受。我近年对书法艺术萌生兴趣,每天也试试习字,而古人是用青毡“衬书大字”(见《长物志》)。《世说》载王献之在书斋夜卧,有盗入室,献之对他说:“青毡我家旧物,可特置之。”书圣父子家中的旧青毡,想来不会用作铺地保暖,是以弥足珍贵。韩愈的《石鼓歌》云:“毡包席裹可立致,十鼓只载数骆驼。”原来曾有人提议用毡包裹石鼓这种至宝之物呢。毡之为用大矣哉。毡屋即蒙古包,毡车即篷车。个人的用品有毡帽、毡袜、毡靴、毡笠、毡笔、毡裘;家中则挂毡帐、毡帘。至于毡墨,可模拓碑文及古器图形。
毯字的出现,远溯自唐代,《补江总·白猿传》有:“嘉树列植,间以名花,其下绿芜,丰软如毯。”那时,毯与地还未组成一词,却和毡合用。白居易《青毡帐二十韵》诗句:“软暖围毡毯,枪束管弦。”到了清代,红楼梦第七十六回:“贾母又命将毡毯铺在阶上。”毡毯合称,用途有别。地毯的名称,要到元代才正式登场。《元史·世祖皇后察必列传》中记载:“宣徽院羊臑皮置不用,后取之合缝为地毯。”这段文字所记的地毯,显然是铺地的羊皮,而不是栽绒地毯。可《大元毡罽工物记》中就记载了各式地毯的制法与颜色,泰定年间的记载是:“赴中尚监资成库送纳成地毯六扇”、“西宫鹿顶殿地毯大小二扇”、“成造地毯四扇”等。
《飞毡》一书中所叙述的毛织品,是地毯,为什么称为毡呢?《说文》说得好:“氍毹、毾,皆毡之属,盖方言也。”小说中的肥土镇,有自己的方言,对于毛棉绒丝织成的铺垫物,不管是平纹或栽绒织法,不管是为人取暖、覆盖、供人欣赏,包裹东西,作为书写的垫子,以至纯为踩踏之用,一律称之为毡。店铺的招牌上明明写着地毯铺,可肥土镇人称为地毡店,无论毡毯,都叫它毡。这不完全是虚构,我生活的地方,一直毡毯不分,都读成“煎”。所以,小说从俗,名为《飞毡》。至于内文毡、毯并用,则略有分别:正常叙事,用毯;如由肥土镇人口中陈说,则用毡。
打开世界地图,真要找肥土镇的话,注定徒劳,不过我提议先找出巨龙国。一片海棠叶般大块陆地,是巨龙国,而在巨龙国南方的边陲,几乎看也看不见,一粒比芝麻还小的针点子地,方是肥土镇。如果把范围集中放大,只看巨龙国的地图,肥土镇就像堂堂大国大门口的一幅蹭鞋毡。那些商旅、行客,从外方来,要上巨龙国去,就在这毡垫上踩踏,抖落鞋上的灰土和沙尘。可是,别看轻这小小的毡垫,长期以来,它保护了许多人的脚,保护了这片土地,它也有自己的光辉岁月,机缘巧合,它竟也会飞翔。蹭鞋毡会变成飞毡,岂知飞毡不会变回蹭鞋毡?
这书的写作,曾由朋友替我向香港艺术发展局申请资助。资助通过后半年,忽然产生一些古怪的议论,让我看清楚了某些人情物事,而这,未尝不是多年来努力编织这毡的额外收获。
西西,原名张彦,广东中山人。1938年生于上海,1950年定居香港,毕业于葛量洪教育学院,曾任教职,又专事文学创作与研究,为香港《素叶文学》同人。著作极丰,出版有诗集、散文、长短篇小说等近三十种。1983年,短篇小说《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获联合报第八届小说奖之联副短篇小说推荐奖。1992年,。1999年,。2005年,继王安忆、陈映真之后获世界华文文学奖,获奖作品是长篇小说《飞毡》。2009年,《我的乔治亚》、《看房子》入围台北国际书展大奖。2014年获得台湾“全球华文文学奖星云奖之贡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