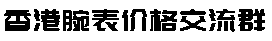“那些消逝了的岁月,仿佛隔着一块积着灰尘的玻璃,看得到,抓不着。他一直在怀念着过去的一切,如果他能冲破那块积着灰尘的玻璃,他会走回早已消逝的岁月。”
这是电影《花样年华》最后打出的字幕,那一年,是千禧2000年,我在尖沙咀看这部片的首映,我不知道刘以鬯先生有没有坐在王导旁边看这部电影,但是,那非常醒目的对刘以鬯先生的致谢字句,打在如走马灯的荧幕上,却是观众不会错过的。
是的,许多人初识刘以鬯先生,都是因为王家卫。王家卫的《花样年华》的叙事灵感,取材于刘以鬯的中篇小说《对倒》。
2018年6月8日,刘以鬯先生逝世,享年99岁。
刘以鬯(1918年12月7日—2018年6月8日)
王家卫除了在个人微博贴文,以电影《2046》借用《酒徒》内文字的一句:“所有的记忆都是潮湿的”悼念刘以鬯先生,后来亦发表感言:
“很婉惜。刘以鬯老师的离去象征了战后南来作家在香港异地开花之时代的终结。香港为这一代的文化工作者提供了一席之地,容他们在此开花结果。再一次对相继离世的饶宗颐大师、林燕妮女士以及刘以鬯先生这些前辈致敬。”
王导曾电影专书中提到:“ 我对刘以鬯先生的认识,是从《对倒》这本小说开始的。‘对倒’的书名译自法文‘tête-bêche’,是邮票学上的专有名词,指一正一倒的双连邮票,对我来说,它不仅是邮票学的名词或是小说的写法,它也可以是电影的语言,是光线与色彩、声音与画面的交错,甚至可以是时间的交错,一本一九七二年发表的小说,一部二千年上映的电影,交错成一个一九六零年的故事。”
而之后的2046,亦被称深受刘以鬯的另一本小说《酒徒》所影响。
刘以鬯原名刘同译,1918年12月7日生于上海,1948年来港定居,中间曾在重庆、上海、新加坡等地当报纸副刊编辑,以及杂志社、出版社的总编。他曾主编《香港文学》月刊十五年,直到2000年才换手。他17岁就发表小说《安娜·芙洛斯基》,30岁定居香港后,写小说、散文和评论。他的一生,和文字为伍,是那时香港报纸,副刊编辑也是作者,那年代,香港报业发达,副刊受重视,武侠小说、言情的、情色的,百花其放,有名的作家都在各家的副刊有一个连戴专栏,一天交出万字稿子没有问题。他一直到出版社经营不下去,才正式以写稿为生。
像《花样年华》的周慕云,俯桌疾书的专注模样,看来也是拿刘以鬯先生做人办。最初的原型就来自这个写稿佬。幸而,刘以鬯先生也写小说,,但书出来了,印数不多,他也担心可能绝版后再不见天日,他自己说:“香港报纸的负责人多注重经济效益,刊登的连载小说必需有离奇曲折或缠绵悱恻的情节去吸引读者追读,像对倒这样没有纠葛的小说,纵有新意,也不能得到报馆方面的赞许。”所以写了一百多天,11万字,就自动结束了。
《花样年华》剧照
那是1972年,他采用的新颖手法与叙事氛围,没人欣赏鼓掌,但近五十年后的今天,《对倒》和他的《酒徒》这两个最受注意的小说,已经成为香港甚至华文文学史一个非常重要的条目,而他,不仅是香港书展及文学节第一届年度文学作家,成为各地文学讨会的讨论重点,他已然是香港文坛最备受尊崇的前辈。
时间很残酷亦很公正,它淘汰了那时在香港副刊眼花撩乱的各式书写,只留下几个可以留名的人物,刘以鬯先生在香港纯文学的地位崇高,所有知名的作家与评论者皆因他小说的创意与打破传统叙事,而视为先锋。他比那时代的香港文学走前了好几步。也斯、罗贵祥、黄淑娴、董啓章、许子东甚至导演杜琪峰,他们在刘以鬯先生的专书:《刘以鬯与香港现代主义》《刘以鬯全卷》皆立文以赞之。他的小说让我们可以寄居于梦想或回忆之中,而不受鄙视;可以做为一个边缘者,而更清醒;可以让香港的主流书写,终于承认这也是一种香港的面貌、香港的描述,甚至更具审美观与历史感。
像《对倒》,以一个老男人淳于白和一个少女亚杏的故事。描写一对互不相识、毫无关系的男女,男的已经老去,女的则正值青年少艾,他们在一个晚上不约而同地来到旺角,并排同坐看同一场电影,然后又分开了。当天晚上,两人都做了一个绮梦,男的梦见自己变回年轻时的样子跟少女做爱,女孩则梦见跟一名英俊的男子做爱。两人虽然无法满足现实,却皆满足了幻想。一正一负,两线平行的叙事手法,是现代主义也,是虚无的描写,而以他们两人眼中所见的七零年代的香港,如此细致而真实,他们是本雅明所说的游荡者,他们撷取着香港的巿井街廓,一个只剩回忆,一个充满梦想,如此错倒并无所意旨的小说,看似空幻,却以空幻填满了空幻。
刘以鬯的另一本同具名望的小说《酒徒》,被称为香港,甚至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发表于1962年,它是一人的独白,里头四十二章节,长的一章有近万字,而短的只有十二个字。刘以鬯先生彷彿走得太快,在那时已完成前卫的新局面,让后来者嘡舌无语。酒徒的自白,像一首首短诗:“我必须抛弃过奢的欲望,让过奢的欲望,变成树上的花瓣,风一吹,树枝摇曳,飘落在水面,慢慢向前流。我必须忘记痛苦的记忆,痛苦的记忆变成小孩手中的汽球,松了手,慢慢向上升……”
《酒徒》剧照
另外《打错了》《香港居》《吵架》《我与我的对话》和散文《错体邮票》《尖吵咀钟楼》……这些文字与场景,经过了几十年,与所有的现代香港文学几乎相应相叩,毫不违和。
他的现代主义、他的文不载道,在1960年代的殖民地香港,结合而成一种异国的特殊情调。我看刘以鬯先生的小说,好像看一部部法国新浪潮电影,楚浮、高达、侯麦、马卢的影像,都移植到香港这个拥挤而匆忙的城巿,那些可以说的不可说的感觉与情意,都沉浸在深深的海底,像维多利亚港四月的浓雾,你看不清楚的,刘以鬯用文字帮你梳理,我们像在走一个没有目的的旅程,若你跟着他走一回,你会恍然知晓,某种属于香港的、个人的一段心路,似远还近,似模糊却清晰。
这是九十九岁的刘以鬯先生,予香港文学最好的礼物,予文学最诚挚的敬意。
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