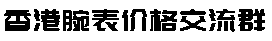侷住香港系列报道二:劏房人家
劏房之小已经使我们唏嘘不已,而劏房住户们的生存之艰和人生跌宕则更让我们感慨万千:
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每晚11点躺下的伦叔常常在凌晨1点时仍未入睡,房间狭窄而不通风,他被闷得睡不着觉;
尽管知道北河烧腊店的饭菜好吃又便宜,但伍伯仍然只是在自己的板间房里蒸熟饭菜解决三餐,因为从他的住所到北河街需要坐车,每月只有政府综援收入的他负担不起交通费;
陈华基本不与邻居聊天,而是喜欢一个人呆在板间房里看电影,又或者是在Facebook 上回忆他的演艺事业……
极度有限的生存空间、紧缩的经济处境、与人群的疏离,以及入住劏房前的风雨人生,一股脑儿集结成硕大无朋的阴影,笼罩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劏房如打包箱般将这些住户们紧紧包裹,而在我们看来,被侷住的不止他们的肉体,还有他们的处境。
逼仄「同居」
对于住在劏房里的人来说,床的用处十分多元。陈华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双层床,他平时睡在下铺;醒着无事可做时,他要么趴在床上玩手机,要么盘腿坐在床上抽烟、喝啤酒。有一次,当我们敲开他「吱呀吱呀」叫着的木门时,他正蹲在床边吃东西,床铺充当了他的饭桌,上面摆着的外卖盒里盛着油滋滋、红彤彤的米线。陈华自己也觉得这么吃饭有些难为情,把门忽地一下又拉上了。
板间房是用木板隔开的,且上下都留有空隙,因此,安仔和陈华不仅共用厨厕,还共享邻居的声音。我们在安仔家拍照时,对面的住户房门紧闭,但木板门藏不住动画片里稚气的配音。几分钟后声音断了,后来又变成了新闻播报的声音。安仔喜欢在自己的房间里弹吉他唱歌,被迫成为听众的陈华无奈地摇了摇头:“他唱歌真的好难听。”而安仔则对我们嘀咕着:“陈华晚上老是不关灯睡觉。”邻房的灯光透过木板的空隙,让安仔不得安眠。
与安仔、陈华不同,张女士在鸭寮街的住所有14平米,与两平米的板间房相比,可谓「豁然开朗」。但屋子到底逼仄,房间里的家具都是迷你型的,电视机直接挂在了墙上,吹风机与马桶的大小只有正常尺寸的二分之一。借用厕所时,我们生怕一不小心,马桶就被压塌了。
| 劏房内,厕所紧挨厨房 |
张女士的劏房让她在空间上完全拥有了私人空间,但薄薄的隔断墙无法将她与邻居的生活彻底隔离——只要张女士呆在家里,左邻右舍的争吵、小孩子半夜的哭闹便不绝于耳。
这几位住户的房间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没有阳台。伦叔每天在公共卫生间里洗完衣服,便将衣服晾在他住的那层楼的露台上,准确地说,那是一个布满污水、堆满了废建材脏纸巾的平台。衣服晾在晾衣绳上,与底下的脏污近在咫尺。
而张女士已经逐渐适应了下班打开家门时,扑面而来的那股潮湿的霉味。她的劏房楼下是面食作坊,废水倾倒在街面上,在空气中发酵出恶臭,张女士只得一年四季将窗户紧闭。房间没有阳台,屋里的通风仅靠房间内一年四季不停的风扇进行。张女士洗过的衣服就晾在室内。每次出门前,她得把手伸进挂在头顶晾衣绳上的衣服里,一件件地检阅一遍,直到摸出一件彻底阴干的衣服换上。
| 张女士家里晾着的衣物 |
人在窘途
“劏房住户们最大的困难?当然是经济困难。”SoCo资深社工施丽珊不假思索地答道。
“走,我带你们去吃好的。”第二次见面时,伦叔带着我们来到了他家楼下的三洋餐厅,大喇喇地坐到了空位上,手一挥:“服务员!点餐!”然后招呼着我们点菜。我们看了半天菜单,才咬牙点了菜单上最便宜的鸡肉焗意粉,然而这也要40多港币,而伦叔则点了一份标价78港币的咸鱼茄子煲,这个价格在深水埗算很高了。这天,政府5000港币的综援刚打进伦叔的银行账户,他允许自己吃一顿好的。
“你看我平时笑嘻嘻的,好像很开心,其实要不是政府养着,我早饿死了!”一次聊天里,伦叔向我们坦白了他的经济困境。如今64岁的伦叔几乎没有存款,所有的收入只来自于政府综援与散工收入。他已经彻底错过了自己生命中赚钱的好时代。
| 伦叔 |
80年代时,伦叔在制衣厂里做熨衣工,工厂加工量大,且实行计件制,伦叔的月薪有五千港币。同时期,一间面积为五十平方米大的房子,价格在七、八万上下。许多香港老工人在那时买上了第一套房。80年代后期,香港的工厂北迁到大陆,伦叔转行做装修。90年代时,他在酒店里找了份稳定的装修工作,月薪一万一。假如伦叔在当年稍微留心存点钱,现在也不至于家徒四壁,然而伦叔却将钱都花在了赌博上。输赢在当时他眼中没什么大不了,“反正有干不完的活,今天输钱,明天也能多干点赚回来。”
90年代,工资涨了,他赌得更大了,甚至和朋友共赴。澳门葡京酒店的赌场金碧辉煌,赌桌上红红绿绿的筹码涌过来,又流过去,有一夜,他输了7000块。输得越多,就越想赢回来。伦叔不停地加注加码,一次,两次,三次,直到他透支了信用卡,欠下14万的债。
和伦叔一起赌博的两个朋友欠了高利贷,最终一个跳楼,一个自缢身亡。生怕自己也被追债,伦叔辞职,取出了工作岗位的公积金还债,债务还清后,他只剩一万元家当。没了钱,伦叔搬进了800块一个月的床位房。在那里,他只有一张四面被包围在破旧木板中的床。夜晚躺在床上,木虱出没,咬得他无法入睡,睁眼到天明。直到后来接到了些散工,伦叔的境况有所好转,才辗转搬进了深水埗的板间房。
回首往事时,伦叔不停抬手抓弄着头发,手指穿插在覆盖不到前额的几缕稀疏头发中,一下下地捋着。“如果不是因为读不了书,我又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伦叔说。小时候,父亲烂赌,伦叔小学二年级就辍学到洗头铺打工,在同事的影响下买了且赢了人生中的第一支马,并沉浸在赢钱的快感中,13岁便重染父亲的恶习,堕入赌博的深渊。
“一直赌,一直赌,输到现在这副样子。”说完,伦叔冷笑一声。他扭头望了望他供着的观音道:“下辈子投胎,我一定不要赌。”
| 回忆往事时的伦叔 |
孤独之境
摄影师Benny Lam与SoCo合作了《侷住》摄影集。每当回想起当时的拍摄经历,Benny Lam 记忆最深的是一种精神的束缚:“住在劏房不仅是物理层面上的侷住,精神上也被侷住了。 ”
在医院里做清洁工,下了班或周末时同事喜欢去聚会,但张女士从不参加。她说:“她们有房子,我还得租房,在香港,你没钱,就不要社交。你不需要那么多朋友。”她也从不向同事提起自己的境遇。“知道你住劏房,她们会瞧不起你,觉得你住劏房很恐怖。”张女士严肃地告诉我们。张女士是3年前不堪家暴而离婚后搬入劏房的。生意破产的前夫时常对张女士拳脚相向,他曾抓着她的头就往门上撞,张女士的额头上顿时起了鸡蛋大小的包。
若是放假在家,张女士便会在房子里呆一整天,懒洋洋地盯着电视换着一个又一个频道。邻居们也都大门紧闭,互不往来。
与张女士一样,伍伯在周末无处可去。如今已经92岁的他一个人住在元州街的劏房里。20年前,做了一辈子三行工(泥水、木工、油漆,俗称三行)的他攒下20万投在买楼花上。然而亚洲金融风暴袭来,香港楼价暴跌,伍伯以亏空20万的代价,永远失去了买楼的机会。
因为投资失败,伍伯与家人决裂,离开了家,在劏房里一住就是20年。如今,儿女与孙女并不经常来探望他,去年,他的老伴也因老年痴呆住进了养老院。独居劏房里,伍伯随时会有生命危险,他的床边有个红色按钮,那是他的「救命武器」,一旦身体不适,只要按下按钮,便会有社工来帮助他。但伍伯按得更多的是他这栋楼电梯里的报警器,他住在10楼,电梯常坏,每次被困在电梯里等消防车时,他得孤零零地等上近一个小时。
| 伍伯 |
托尔斯泰曾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与张女士和伍伯相比,陈华的孤独又是别一番滋味。
因为长年酗酒,陈华的脸泛红而浮肿。他的眉毛浓而杂乱,双眼皮的褶皱宽而深,眼底有深深的倦态。
| 陈华 |
总是喜欢跟我们强调“我是一个演员”的陈华今年43岁,但其实,他36岁时才入的演艺圈。入行前,他四处打散工,甚至混过。8年前,他帮朋友的忙去做了一次临时演员,演员这份工作让他兴奋莫名:“每天去不同的地方,拍不同的东西,好玩。”于是陈华入行,从临时演员做起。
后来,陈华和前女友合伙开了一家演员中介公司,生意红火,年入50万。然而,女友不理解他对演戏的执着,搞砸了陈华难得的一次与偶像刘青云对戏的机会。于是,陈华愤而与女友分手,走的时候只带走了一个背包,没拿走一分钱。背包里,除了身份证件,还装了他演戏的剧本,以及一件刘青云穿过的戏服。
“呐,这件。”陈华从床的上铺摸出一件灰色牛仔外套,将它抖落开,展露于胸前。他低头看着外套,嘿嘿笑了:“我连自己意大利进口的皮鞋都没有带出来呢。”语气中没有可惜,却满是得意。
| 陈华身着刘青云戏服 |
与女友决裂后,陈华无家可归,在社工的帮助下住进了如今的板间房。如今的陈华还是打散工——他怕找到了稳定工作,会错过可能有的试镜机会,然而找他拍戏的人已经寥寥。
陈华曾在 Facebook 上将港片比作“我最爱的恋人香港电影”入行之初,满脑子都是经典香港影视剧的他看不惯圈内苟且赶工的作风,在片场经常当面指出导演的不是,甚至破口大骂:“你拍的什么狗屁!”有一次,他还拎起垃圾桶往导演身上砸。在片场的表现渐渐地败光了陈华在圈内的资源。
如今没戏拍的时候,陈华选择窝在房间里看电影碟片。他在社交账号上分享了孟浩然的《留别王维》。在这首绝句里,他拉红标注了倒数第三句诗:知音世所稀。
| 陈华Facebook截图 |
陈华从他一袋子的影碟里挑出一张《南海十三郎》,说这是他最喜欢的电影。影片由真人真事改编,主角南海十三郎是一代金牌编剧,出生于粤剧世家,曾在粤剧圈内出尽风头,后来时局动荡,他看不惯圈子里的媚俗之作,与同行们不欢而散,最后无人问津,冻死街头。陈华吐出烟圈,皱着眉,“我觉得自己和十三郎很像。”
还有另一部电影也让他想起了自己。尔冬升的《我是路人甲》里,主角沈凯为了自己的横店临时演员梦,不惜让妻子堕胎,最后因戏成痴,精神失常。每当陈华看到这里,他便掉泪——他想到了自己的前妻和儿子。
入行后,演员工作饥一顿饱一顿,陈华不想拖累妻儿,便提出了离婚。除夕夜,他想起了前妻和儿子。他弄丢了前妻的联系方式,而前妻已搬离了原来的家,他再也找不到她和儿子。陈华从钱包里掏出儿子的证件照,手指搓着儿子照片上笑眯眯的小脸:“他长得不像我,但性格跟我一样执着。
“想他吗?”我们问。
他嘴角一撇,想要摇头,仿佛不屑于表露自己的感情,但最终还是微微点了点头,然后深深地吸了口烟,微眯的双眼似乎闪着泪光。儿子的生日是10月28日,陈华一直都记得,但儿子今年已经14岁了,陈华手头的仍是他6岁时的照片。
| 陈华想起了自己的儿子 |
“你们是不是弱智?没有哪个人会听我瞎说一个晚上的。”聊完他的故事后,陈华指着我们嘲笑道。随后,他仰头往嘴里倒了一口啤酒,咽下,然后盯着眼前的烟灰缸,突然吃吃地笑了。我们问他怎么了,他笑着摇头,脸上的表情变得有些自嘲:“没事。”他看了看墙上的钟:“居然已经晚上12点了。我已经很久没有说过这么多的话了。”
送我们出门时,他对我们挥挥手,挑挑眉,一脸的江湖气:“明年春暖花开日,就是我们再会之时。”那是周星驰《九品芝麻官》里的台词。我们谁也没能接上他的话茬。
(本文转自公众号牛犊走笔)
文字 | 李馨婷、杨珊珊
图片 | 番茄侷蛋小组
版式 | 李馨婷、林梦鸽